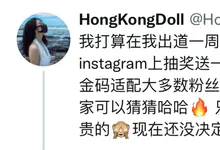「“丈母娘粉”和“嬷粉”两个群体都在通过塑造一个男性的公众形象,对现实生活中的不可承受之重完成自我“消化”。」
“董宇辉你不要再送我东西了!”“完全被董宇辉拿捏住啦!”“董宇辉你的浪漫也太直白了,一套接一套地来!”
最近,董宇辉的直播间成为了无数中年女性和宝妈们的聚集地,她们把自己定位为“丈母娘粉”,在社交媒体上略显笨拙地用买东西、发视频等直白的方式支持着董宇辉的带货事业。
有意思的是,“丈母娘粉”们所使用的话术高度重合,都是在略带娇嗔地“抱怨”着“董宇辉你不要再送我东西了!”,但这些物品实际上大多都是她们自己花钱购买、主动为董宇辉“打广告”的。
通过把自掏腰包买的东西说成“送”,一推一拉之间,“丈母娘粉”们与这个直播间里的男性隐秘地建立起了一份关怀与被关怀、惦记与被惦记的情感联系。
相似地,另一边年轻的网友们则掀起了一场名为“嬷”的狂欢。“嬷粉”们大多数以年轻女性为主体,她们以戏谑、冒犯甚至带有些许侵略性的语言,将吴京、张译、张颂文等一些一贯以正派形象示人的男明星“女性化”,颠覆着传统的性别角色和地位。

(网上的男明星“嬷嬷”们)
董宇辉的“丈母娘粉”和男明星的“嬷粉”看似是两个彼此无关甚至相反的关系模式,可它们在本质上却殊途同归。二者的存在共同揭示着不同世代的女性在面对结构性压力时,如何利用现有的文化符号,开辟出情感的出口,对现实生活中的不可承受之重完成自我“消化”。
01 )
“丈母娘粉”:被看见的精神出口
之前,在类似的秀才和“假靳东”事件中,中老年女性粉丝试图在这两个人物身上建立一种私密的、带有情欲投射的虚拟亲密关系,但与此不同的是,董宇辉的“丈母娘粉”们并非在董宇辉身上寻找恋人身份的投射,而是在寻找一个能够正视和回应她们正当精神需求的倾听者。
这背后是中年女性精神身份被忽视的隐痛。在传统家庭结构中,中年女性常常被期待扮演无私奉献的角色,照顾家人、支持丈夫、教育子女,女性们的价值是功能性的、被劳动衡量的、实用主义的,而自己的情感需求却往往被忽视,没有人关心她们“灵魂的出口”。
就像电影《让娜·迪尔曼》中记述的故事一样,女主角让娜·迪尔曼每天维持着相同的家务劳动秩序,洗碗,采购,喝咖啡,煮土豆,晚餐后和儿子散步,雷打不动,疲惫也麻木。
可直到有一天她因为早起了一个小时而秩序崩塌,一整天都在手足无措的焦虑之中度过,最终爆发式地挥起剪刀,平静地杀掉了躺在床上的陌生男人。对这部被一些人认为“时长太长”“太无聊”的电影有一句知名的影评是“三个小时都忍不了,不知道她忍了多少年。”

(《让娜·迪尔曼》)
牢牢嵌入家庭结构的女性们时时刻刻浸泡在“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的循环之中,她们的言论空间被琐碎的日常占据,她们的情感表达常被归结为“唠叨”,她们对一些问题的自我思考和解读被认为“不切实际”。这种长期的不被听见导致了精神孤独。
而董宇辉在直播间话术中将那些普通的生活用品赋予诗意,以此将原本不可见的、琐碎而流俗的家务劳动和平凡生活描述得阳春白雪,进行了“复魅”。
就像卖葡萄他说“会想到久远的诗和金戈铁马的梦”,卖樱桃他说“一个个樱桃挂在树枝上像散落人间的星星”,卖大米他说“我没有带你去看过沉甸甸弯下腰犹如智者一般的谷穗,但是亲爱的,我可以让你品尝这样的大米。”……
这些话语为屏幕前的中老年女性们提供了一个审看自身日常生活的新角度。她们或许因此被启发出一种点石成金般的、审美式的视角,学会了从更高的维度出发,带有赞美地看待自己原本认为平庸的生活。

(董宇辉的带货“话术”)
所以,对董宇辉的“爱”成为了中老年女性们对现实中无人关心她们精神世界的一种疏解方式,一种消化与出口。
这种“被看见”和“被听到”的时刻,就像《好东西》里流传最广的家务劳动片段,当有人意识到女性的需求不再是“囿于厨房与爱”,那么它也可以变得浪漫和崇高,如宇宙般广阔磅礴。哪怕这种“意识到”可能并非是董宇辉主动的、有意的,而只是女性们需要一个可以如此解读的出口。
而将这种情感冠以“丈母娘”之名的表达方式,可以说是全网独一份的。喜欢董宇辉的中老年女性们自称为“丈母娘粉”而非“妈妈粉”,或许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母子关系大多伴随着巨大的、具体的劳动和牺牲,对母亲们来说是一场漫长的“修行”。
而董宇辉这种理想化的、“从天而降”的“互联网女婿”则直接给“丈母娘”们带来了一份可以纯粹欣赏、享受和投入的跨代际关系。
她们在这个男性形象身上体会到了一种在现实亲子关系中往往延迟满足甚至可能缺失的、作为尊长的优越感,以及母亲本能般期待的被反哺的快乐。
他的踏实、成功和博学都是“别人家”培养的成果,自己无需付出养育的成本和辛劳,便可以轻松地享受到一个理想型子孙辈带来的满足感和情感慰藉。

(三联生活周刊的采访内容)
而从传播的视角来看,董宇辉的”丈母娘粉”在网上之所以被梗化、奇观式地传播,一部分原因也是当下的互联网语境中少见、或者说很少容纳这种并“不好看”的爱。
互联网话语场里最普遍的、声量最大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世代,他们掌握着梗文化的生产与传播权,定义了什么是“潮”或“土”、什么是“高级”或“尴尬”的情感表达。而掌握了话语权的群体,会不自觉地将他者的情感经验边缘化、标签化甚至污名化。因为无法理解,所以将其简化为“梗”并进行旁观甚至嘲笑。
在这种语境下,“丈母娘粉”对董宇辉那种略带笨拙、“不入流”的爱就成了一种异质性的存在,无法被现存的比较主流、符合大众审美取向的浪漫爱模版所容纳进去,因此显得颇为失语,甚至沦为笑料。
02 )
“嬷粉”的平行宇宙:对传统性别关系的消化
与董宇辉狂吸中老年女性“丈母娘粉”相似的一个现象是,另一边,当下年轻女性们之中正在兴起“嬷粉”群体,她们将一个个男明星去雄化或女性化,用看似夸张、侵略性的语言去调笑他们,将其纳为自己下位的欲望对象。
“丈母娘粉”和“嬷粉”的相同之处是两个群体都在通过塑造一个男性的公众形象来完成对传统性别角色的“消化”。“丈母娘粉”消化的是价值感失落、精神世界被忽视的压力,只好通过建构精神偶像来为自己正名。而“嬷粉”消化的则是被物化、被审视、在现实性别处境中常常处于下位的压力。
对于“嬷粉”来说,这种快感来自于暂时获得现实中不可得的权力体验,在生活里,她们可能往往面对着职场中的不平等甚至歧视、容貌焦虑、婚恋市场的“估价”等等无处不在的结构性问题,因而通过互联网上的“嬷”将这种压力内化、咀嚼之后,再以相似的方式返还给一个遥远相隔的男性形象。

(“嬷”语录)
然而二者的行为模式却是相反的,“丈母娘粉”倾向于自下而上地建构,将董宇辉高高举起,通过理想化的投射来安放现实中积压的情绪。而“嬷粉”则看起来全然是自上而下的解构,她们主动主宰着一种性别和权力的逆位关系,试图将旧有的神坛变为如今嬉闹享乐的乐游原。
她们闯入旧有的男性权威领地,通过言语上的冒犯和“贬损”对男性形象进行女性化,施加压迫感,争夺话语权。在“嬷”的过程中她们不再是欲望之客体,而成为了观看者,成为了评判和消费他人的“主体”。
但这也只是象征性的。这种性别逆转行为看似是激进的、先锋的权力倒置,但其实这些“套路”仅仅停留在复制而非创造。“嬷粉”们用挑选、物化和侵略的眼光与言语去戏谑男明星时,所使用的语汇和姿态完全复制自传统中男性凝视和消费女性的那一套规则。
可一旦使用这套语言体系,就在无形之中承认并且强化了这套逻辑本身的威权性,仿佛这是手边唯一的武器。“嬷粉”们只是在用现实中最大公约数的“被对待”的行为方式去“嬷”他人。
就像上野千鹤子说对弱者展开想象是强者的特权,“嬷”没有创造出新的游戏,新的性别互动规则,而是仍处于现实生活里“被想象”的惯性之中,继续沿用父权制原有的脚本和工具,学习着扮演着“上位者”。
总的来说,“嬷”仍是一场以父之矛攻父之盾的“展演”,仍被困在主奴辩证的来去之间。就像让娜·迪尔曼日复一日生活中少有出现的那些蓝调时刻一样,看似亮过一瞬间,转而又会陷入一片苍白。而人能做的只好是隐秘地期待着,会否有拿起剪刀的那一天。
(图片素材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