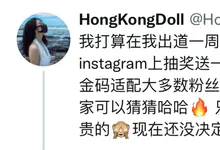放眼整个华语影坛,很少有明星像舒淇这样特殊。
当她在银幕上大放异彩时,正值两岸三地电影文化交流最密集的时期,我们在她身上看到了不同地区电影产业的交融印记。
出生于台湾的舒淇,最早被香港娱乐产业发掘,成为其没落前为数不多的闪耀面孔。
成名后的舒淇并未满足于固守既有形象,她与侯孝贤的合作,不仅巩固了她在华语电影中的地位,也为台湾艺术电影将长青状态的延续贡献力量。事实上,她成为这位华语电影大师后期创作的银幕缪斯,出演了他在00年后的多部代表性作品。

在中国大陆电影迈向产业化时,舒淇又先于他人来到这个新鲜的环境接受挑战,内地观众终于得以在大银幕上领略她的明星风采。
可以说,舒淇精准踩中了华语电影每个上升期的节奏,成为华语影坛极少数能连接整个华人文化圈的现象级明星。
所以,当她决定做导演时,也绝非一次简单的玩票。
《女孩》是舒淇的导演首作,这部融入她个人成长经历的作品,还原了80年代末台湾地区的社会氛围,也延续了台湾电影一贯的家族叙事。女孩在原生家庭的折磨中经历成长,构成这部影片的悲伤基调。

今年夏天,《女孩》成功入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这是国际影坛对导演舒淇的巨大肯定。随后,她又在釜山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导演。对一位新人导演而言,她的首秀就已展现出非凡的光芒。
经历了如此成功的起步,舒淇由衷的向时光网感慨道:“其实我真的感觉自己是特别被上天眷顾的一个人。”
11月1日,《女孩》正式公映。时光网与舒淇坐下来,聊了聊这部电影,以及它为她带来的种种惊喜。
完整采访视频:

认真开始做导演
在经历了香港明星工业的包装后,舒淇成长为90年代最亮眼的银幕明星,但真正令她的演艺生涯更进一步的,则是返回台北后与侯孝贤导演的合作。
入围戛纳的《千禧曼波》令舒淇收获来自全球的目光,《最好的时光》则为她带来了演员生涯最具说服力的认可——金马奖最佳女主角。两人的成功合作也为舒淇拿起导筒埋下了伏笔。

舒淇告诉时光网,侯孝贤的“催促”是她决心做导演的契机。“应该说,是侯孝贤要我做导演我才想到要做这件事,之前从来没有想过会做导演。隔了几年后,他问我开始写剧本了没有。”
意识到侯导的提议并非玩笑,舒淇开始认真思考做导演这件事,而她面临的首个挑战,便是剧本。毕竟,从表演到剧本创作,意味着要自己构建一个世界。
侯孝贤的建议打消了她的疑虑:一支笔,一张纸,想到什么就写下来,慢慢拼凑,故事原型便打磨了出来。
从2015年开始,舒淇开始将脑海中的思绪一一落在纸上。和许多新手导演一样,她的创作起点源自自身的成长经历。尽管这些经历是私人的,但正是这种真实感,为故事注入了动人的力量,也让影片在观众面前闪现出独特的温度与生命质感。

《女孩》的故事背景设定在1988年的台湾省基隆市,银幕上的主人公林小丽,正处在迷惘的成长边缘。酗酒的父亲与痛苦的母亲营造出压抑的家庭氛围,怀揣心事的少女,迫切寻找着负面情绪的宣泄口。
而这些,也映射了舒淇自身的经历。十几岁时,她便离开家乡,独自踏入复杂多变的娱乐圈,那份早早独立的勇气,正如林小丽在银幕上所经受的挣扎与坚韧。
这份银幕上的坚韧,折射出舒淇在执导影片时流露出的责任感。
“原生家庭对于小孩未来成长特别重要。如果有一对父母看了我的这部电影,突然意识到原来不可以这样对小朋友,应该是用爱的教育正确的去关怀小孩,能让小孩子有快乐的童年,我觉得这就是我非常大的成就感。”

从剧本到银幕
2024年4月,《女孩》进入紧锣密鼓的前期筹备阶段。
故事发生在夏天,因此所有拍摄需要在8月底前完成。舒淇和剧组需要在三个月内完成所有的准备工作,这就包括了复杂的置景。

置景的难度在于还原80年代末台湾地区街景的时代氛围,当时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遍布街头巷尾的各种交通工具是这一时期的缩影。
在《女孩》剧本的开场戏中,舒淇原本设计了少女时代的母亲坐在巴士上,与女儿林小丽不期而遇的场景,以打破时空桎梏的方式,将两代女性的经历与情感悄然相连。
这个创意设计在实拍过程中就因为道具的限制无法实现,虽然剧组找到了那个年代的巴士,但却无法行驶。初做导演的舒淇随机应变,将这一桥段改为少女时代的母亲与林小丽在奔跑时擦肩而过,既绕开了客观条件的限制,同时保留了这个创意。
“有很多场景跟我剧本上不符合的东西,最大的困难就是怎么样又可以还原,又可以把它拍出来,这个对我来讲是最困难的。”
相比置景的困难,《女孩》在选角方面要顺利很多。

关于父亲的角色,舒淇的第一人选是曾出演过《当男人恋爱时》《谁先爱上他的》的演员邱泽,他在这两部影片中游刃有余的表演令她印象深刻。虽然一开始担心因为角色形象较为负面对方会拒绝,但邱泽在接到邀请的第二天,就爽快答应了合作。
在这部女性视角的影片中,邱泽的戏份难度不大,却十分关键。舒淇与邱泽的沟通大多落在如何用细节去塑造人物。
比如,舒淇要求邱泽将沙发当做“专属领地”,因为父亲每天醉酒回来都会径直睡在这里,烟灰缸随时都在他的手边。这些生活化的细节,让角色对空间的熟悉感自然流露,举手投足间都要带着随意与惯性。
对于邱泽的表现,舒淇也十分满意,“隔着银幕我都可以闻到他身上浓浓的酒味。”

饰演女主角林小丽的白小樱,则是童星出身。在舒淇原来的剧本中,林小丽在学校与家庭里呈现出反差的性格,但在选角过程中很难找到适合的小演员,直到遇到了白小樱。
“可能是她的黑眼圈,让我觉得就是会躲在衣柜里的女孩。”
根据白小樱的性格,舒淇对角色进行了调整,将学校里开朗的一面拿掉,最后呈现在银幕上的,是一个孤独清冷,没有安全感的孩子,似乎这个世界上没有她的容身之处。白小樱用细腻的表情和动作,将林小丽的孤独与脆弱呈现在银幕上,让观众感受到女孩内心深处的无助与孤寂。

蜕变与认可
从演员到导演,是一次从被注视到注视他人的转变。从镜头前的情感表达,到镜头后的整体把控,舒淇不再只是角色的诠释者,而要成为世界的建构者。

在身份转化的过程中,制片人叶如芬是舒淇强有力的后盾。这位制片人曾经运作过《大佛普拉斯》《阳光普照》等近些年台湾影坛的代表性作品,她的帮助不仅体现在制作经验与资源的支持上,更在于给予舒淇创作上的信任与空间。
“她会先跟我做心理建设……跟我说会发生什么。真的有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还有她在,她会跳出去帮我解决。”
告诉舒淇《女孩》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也是叶如芬。“她跟我讲,‘我们入围威尼斯了,但不要高兴的太早’,我问‘为什么’,她就说‘你知道我们入围的是主竞赛吗!’我觉得自己好像飞到了天上去。”

随后的这段旅程,舒淇回忆时仍然不自觉地流露出幸福与喜悦。《女孩》不仅在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首映,与吉姆·贾木许、凯瑟琳·毕格罗、朴赞郁等导演同台竞技,在随后的釜山电影节上,舒淇更是获得最佳导演。
考虑到釜山电影节在东北亚地区的重要性与专业性,可以说这既是对《女孩》艺术完成度的肯定,也是对舒淇转型的专业认可。
“电影节是非常看评审的喜好跟爱好的,刚好我拿奖的那一轮评审,可能就是喜欢这个风格,所以就拿了奖。其实得奖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所以这一整串的旅程是我没有预料到的,没想到一开始就会有这么多惊喜。确实,我到现在还没有从这些惊喜中缓过来。”
整个过程充满艰辛和惊喜,舒淇也坦言,相比做演员,导演的工作压力更大,她不仅要感性创作,还要理性执行每一个细节。

临近采访结束时,舒淇坦言,未来是否继续做导演,还要看《女孩》的票房表现和资源情况,但她不会偏离自己的创作本心,依然会拍摄文艺片,讲述和她自身相关的故事。对于导演舒淇来说,《女孩》仅仅是开始,也许还会有更多惊喜,值得我们的期待。
【点击往期回看】